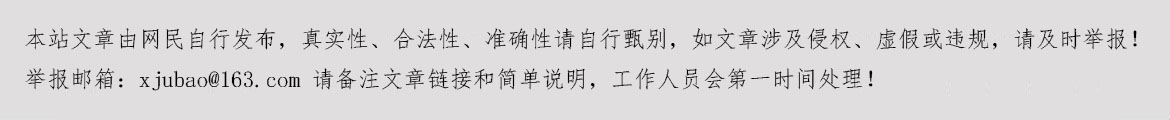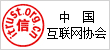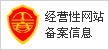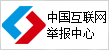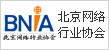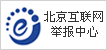那年,我当兵离开家的时候,父亲给了我6元钱…
2022-10-23 16:15:02
我的高原军旅生活张登科
点击进入:1、一心想当兵
2、我勇敢地离开了家乡
三月一日,是农历的二月二,清早起床后,母亲给我打来几个荷包蛋,做了平时很少有的好吃的,但是看到她眼角的泪水,看到一家人忧愁的面容,想到我今天就要离开他们,奔向那遥远的地方,心情也顿时沉重起来,再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。有很多要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,只能对视着母亲,啥也没说。两个姐姐对我说,去了就要好好干,别给家里人丢脸,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,别太想家。就要走了,我忍住泪水,头也没回的走出来家门,在那种气氛中,只有走了,大家的心才能慢慢的平静下来,儿行千里母担忧,这是人之常情。
到临潼县送兵的任务放到了生产队,哪个队有新兵,哪个队就要派人用自行车送到县城。生产队给送兵的人记工分。我是父亲坚持要自己送上县城的。我含泪走出家门时,母亲没有出房门,她一定很伤心。我走到村子东头的饲养室外面,爷爷站在那里和我告别。那时爷爷已经七十五岁了,在那缺少营养的年代,这真是高寿了。那时爷爷经常说:人活的是五年、六月、七日、八时,这个意思是:人活到五十岁时,以能活几年论;六十岁以上,以能活几个月论;七十岁以上以能活几个日论;八十岁以上以时辰而论了。所以爷爷认为我这一走也可能是和他永别了,再也见不上面了,也就十分的伤感。到了村外,新庄的母亲给了我一些炒面蛋,我终身难忘。家乡的天是美丽的,离乡人的心事痛苦的,为了干一番事业,我勇敢地离开了家乡。
按照新兴公社的通知,这天早上十点钟,全社新兵先到屈家大队的孟家小队集合,然后一起上县城。我和父亲赶到时人还没有到齐,这里除了送兵的社员外,还有一些新兵的亲属,也有个别新兵的未婚妻。我没有正式定亲,也就没有想她来送。人到齐了,公社武装干事讲话,要求路上注意安全,告知我们到县城集合地点。讲话之后,我们大家排成一字型骑车走北屯到栎阳,一路向南行进,到了雨金稍作休息,又继续赶路。到了渭河边上(那时还没有桥),水还比较大,南北的交通靠一条木船来回摆渡。一路上浩浩荡荡也很壮观。但和前几年相比,由于政府工作停顿,所以公社里没有欢送会,没有敲锣打鼓,没有大红花,也比较平淡和冷清。就这样,阎良地区的武屯、北屯、振兴、新兴四个公社的青年用自行车送到了六十里外的县城;就这样冷清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,奔向那火热的军营,奔向那向往的人生。
一路上,我不能老让五十二岁的父亲带着我。虽然我人小力薄。但我不时地换着骑车,一路上虽然春光明亮,但我心情难以言表,一路上很少说话,看着一年年显老的父亲还要继续苦干,想到这我暗下决心,到了部队我一定要非常节俭,把有限的津贴费省下来寄回家里,以减轻父亲的负担。家里能干的就是父亲了。真为家里担心,更为父亲的身体担心,别的大队对当兵的有工分补贴,而同一片天地下,官路大队却没有。真是奇怪,但是也没有办法,拥军的风气还没有到官路。
还是回到过渭河这段。快到渭河了,河滩很宽,水流靠南,河里的道路不平坦,不好骑车,我们推着车子来到渡口,上了木船,每人每过一次五分钱,自行车也当作一个人——五分钱。我坐上了木船,船虽然不大,但也能站三十多人和车子,第一次坐船过河对我来说也充满了好奇,因为这是今生第一次。过了河之后,一路慢上坡,过了新丰就能看见南山(也就是骊山,我们都叫做南山)了。平时在家乡,要是晴天也能清楚地看见南山和北山,但那时远距离,现在离得这样近,我很激动,看到大山的雄伟和美丽。再走路一会,父亲指着山下的一个大土包说,那就是秦始皇陵。父亲虽说没有读过一天书,但平时最爱看戏和听评书,所以对历史上的人和事还是知道一些的。记得我上二年级前后,那时有一本连环画小人书叫《杨家将》,父亲叫我读给他听,我把“佘太君”读成了“佘太君”,我读了一会,父亲纠正我说应该是“佘太君”。我脸红了,一个二年级学生让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纠正错字,真叫人不好意思。
来到县城,我被安排在县委大礼堂住宿,里面没有椅子,空荡荡的地上铺着麦草,留有过道。当天傍晚,他们给每人发了一床军用被子和打背包的带子,没有褥子。晚上就将就地睡在麦草上。被子可以铺半边盖半边,父亲和其他送新兵的社员被安排在另一个礼堂里,住的情况和这里一样,被子是从招待所借的,还交有押金。所有新兵在一起上灶,一份菜,半斤馍,不够可以再领。送新兵的是直系亲属的。每顿饭交半斤粮票不收钱,其他人还需要交些钱,大概两角左右,但是伙食不如新兵灶的,油水少量一些。
原定2号下午能发军服,因互相扯皮,阻力大,听说造反派要加送有关人员入伍,军队方面不同意。最后因第二天军列要来拉新兵,所以军方做了让步,收上来不愿意要的兵。军服也一直拖到4号晚上才发放。由于拖的时间长,父亲的粮票不够了,是水北的张百武借给了我们才度过了这几天,张百武是我们村的女婿,回家之后还他也方便。其他送新兵的人也在等待,因为要捎回去新兵们换下来的旧衣服。
我们新兴公社这次去西藏的有二十四人,分别是水北四人,官路三人,新牛五人,屈家五人,咀子三人,井家二人,万南二人。官路大队的三个人分别是:一队薛君贤,二队是我,八队是韩福田。
三月三号,新兵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,去大众浴池洗了澡。一般上午组织学习,下午自由活动。我和韩福田去上山玩,但没有到山顶,只到了一个叫老母殿的地方就没有力气了。那时华清池的门票是8分钱。上山不要门票。我俩还在捉蒋亭那儿写了一个纸条,夹在两捉蒋亭的解说牌背后的缝子中,上面写着:某年某月某日等字样留作纪念,设想从部队回来时,再取出来看一看。但多年以后再来捉蒋亭那里已经面目全非了。捉蒋亭也更名为兵谏亭,大牌子已经拆除了,自然也就找不到纸条了。从山上看城里,觉得很大很美,山上人来人往,也很热闹。下山后我们又去了华清池。印象最深的是五间厅,那是当年蒋介石来陕居住的地方,玻璃上还保留着西安事变时的枪眼,它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存在,也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的事件。
三月四日下午给我们发了军装,那时军装分1—5号,接兵干部先把新兵从大到小分成4个纵队,5号服装男兵很少用到。我被分到三号队中,后有调整到2号。我是2号队中最小的,自然也就领到了2号军服。其实我在新兵连时个子就长了不少,后来2号衣服很合身。晚上我把换下来的衣服送到父亲那儿。到了父亲那里坐了一会,给他汇报了后面的安排:明天早上坐火车到甘肃省的天水市,在那里训练两个多月后才进藏。父亲给了我6元钱,问是不是到那里就发军饷,我说我也不知道。不过6元钱已经不少了,我只买肥皂、牙刷、牙膏之类的日用品和必需品,别的我不会去买的,我决不会乱花钱的。父亲听了后点了点头。我告别了父亲,回到住处,我想,明天就要离开可爱的家乡,奔向那向往的地方,奋斗自己的人生,为保卫祖国做一个青年人该做的事。
三月五号天还没亮,领导们把我们叫了起来,要求整理好自己的东西,把被子打成背包,把一部分东西也要装进背包,军用挎包,装刷牙洗脸用品,然后去食堂吃饭。吃完饭天才麻麻亮。我们排成队向火车站走去,那时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远,一路上走得很慢,我不时地回头张望,没有看到父亲赶过来,他也不知道走到这么早。到了火车站,火车还没有来,我们坐在站台上等待,在等火车的时候,我多么盼望父亲赶快到来,但是没有,我不失望,我想父亲一定会来的。直到火车进站,我们准备上车的时候,我看到父亲匆匆赶来。推着自行车,车子衣架上捆着我换下来的衣服,在那里焦急的东张西望。我知道那是在找我,因为我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,他眼前一片黄绿色,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我。我赶忙跑出队列来到他跟前,说了声您放心回去吧,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因为别人已经上车了,接兵干部把我叫回到队伍中,我再次回头看来看父亲,就踏上了列车的踏板,走进了车厢。
(未完待续)
(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)
作者简介:
张登科:男,汉族,中共党员,生于1950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,祖籍陕西阎良。1968年—1973年在西藏某部服役。退役后做过会计,进行过个体经营,现居住于陕西西安。喜欢写作。
作者:张登科